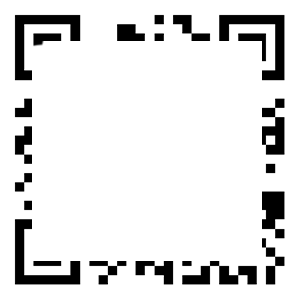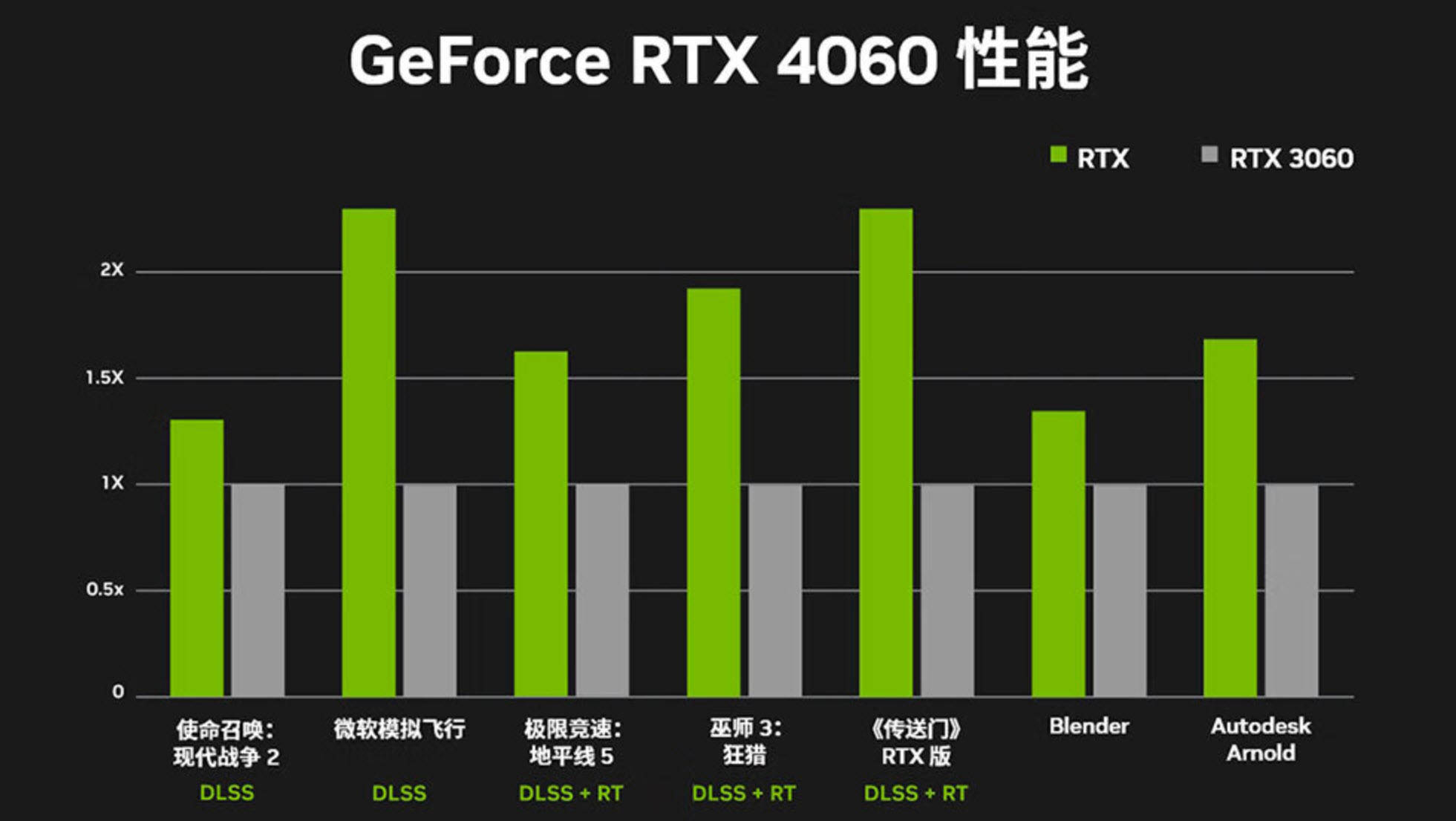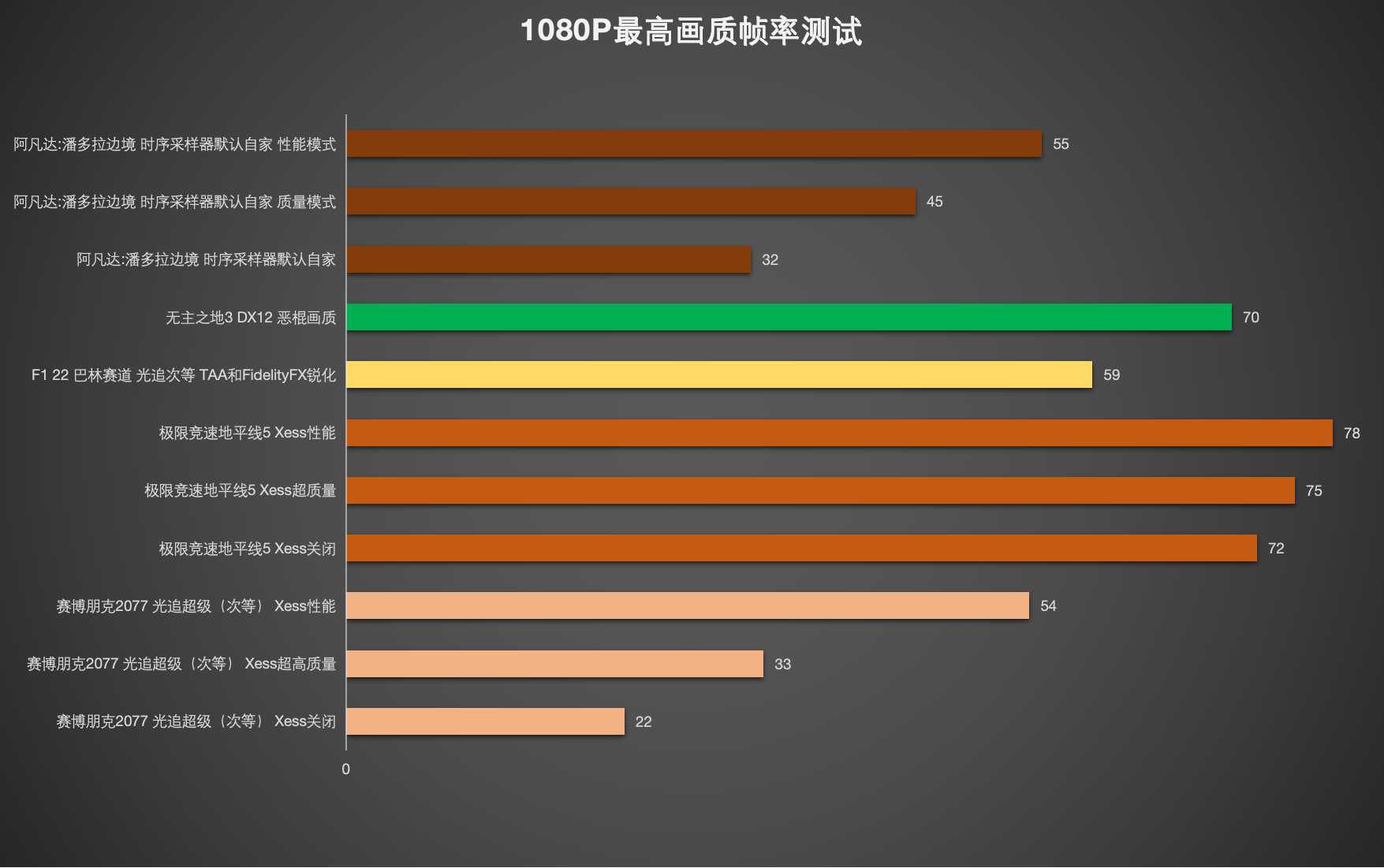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作者(《金大班的最后一夜》)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作者(《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本文通过数据整理汇集了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作者(《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相关信息,下面一起看看。
当台北闹市区西门町处处灯火通明的时候,巴黎舞厅的楼梯上,夜晚响起了高跟鞋的混合泳,由金大班领舞,后面跟着十几个衣着光鲜的舞者,优雅地登上了舞厅的二楼。就在到达大厦门口之前,金大班看见《巴黎之夜》的经理童怀德从大厦里冲了出来。他满脸焦急,搓着手脚对她喊:“金大班,你吃完饭就快天亮了。客人们等不及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提前离开了。”“喂,急什么?这不都在这里了吗?”金大班笑着答道:“小姐们以我为荣,都在和我争双杯。我敢不吃他们的亏吗?”金大班穿了一件黑纱金线的紧身旗袍,一个大道士梳到了头顶上方。耳环、项链、手镯、发夹,金碧辉煌,在她身上到处都是。她的脸上已经挂满了酒,连眼皮都红了。
“你酿的酒我还管得着吗?巴黎的夜场生意总是要做的!”经理童游子一直在抱怨。
金大班听到这句话,在舞厅门口停住了脚,好让那群舞女拿着牌鱼贯进入舞厅。这才把一只手放在门柱上,把自己的鳄鱼皮包扛在肩上,一眼就抓住了童经理。她脸上带着笑容说:“大孩子经理,你个筐!”如果是玩笑,那就这样;如果你认清事实,我今晚就跟你算账。你想晚上在巴黎做生意吗?“金大班在鼻子里冷笑。”别怪我居功:这五六年,巴黎能撑起今天的场面,没有我这个老牌子的玉观音金赵丽?谁挖了花都、肖如意、萧红梅的柱子?你们经理佟大是不是又把华侨姐妹花绿牡丹粉牡丹搬到这里了?这几天报到的大腕,至少有一半是我的老熟人。人们来巴黎是为了花钱,但他们是和你在一起的!另外,我的工资,你是昨天才算的。在这最后的夜晚,我在这里是帮忙,而不是义务。我说一句你不爱听的话:我金去上海百乐门的时候,我怕你连舞厅的门槛都没迈。哪里需要晚上巴黎的大总管来教舞池规则?金大班滔滔不绝地说着,不等佟经理回答,就把舞厅的玻璃门摔了下来。一双三英寸高的高跟鞋踩穿了天空,摇摇摆摆地走了进来。刚进门,几个客人就冲她摇手,一叠“金大班”喊着。金大班没看清谁是谁。他张开嘴,把一个鳄鱼皮包在空中晃了两下,溜进了更衣室。
妈妈的冬收!金大班走进更衣室,手里的手提包当啷一声掉在梳妆台上。他坐在一面大穿衣镜前,痛苦地吐着唾沫。真是没见过世面的红人!巴黎还剩一晚,巴黎还有一晚。说的不好听,但是百乐门的厕所比巴黎晚上的舞池还宽敞,同德的脸和嘴可能没有他在百乐门挖粪坑的份儿。金大班开了一瓶巴黎之夜,在头上洒了一会儿,然后盯着镜子开始发呆。真倒霉,眼看明天就要成为老板娘了,还要被这个臭脏的叫花子打个落花流水。金大班不禁摇了摇头,感叹道。在浪漫场玩了二十年,她找到了一个账号,哪怕能力差了一点。百乐门的紫丁香美人任黛黛嫁给棉纱大王潘的时候,对别人很刻薄:我们紫丁香的手艺很好,抓了一只千岁的甲虫。其实我也不知道潘老头在她的金赵丽上花了多少心血,恐怕金山也买得起一个。那时候我年纪大了,也臭了,都不敢给任岱岱一脚。她曾经向那些姐妹吹嘘:“我还没饿到你要嫁人。每个人都应该拿着一块棺材板。”不过那天在台北遇到任黛黛,坐在她男人拥有的富春楼绸缎大宅里,她看起来像个老板娘。一个丁香胖得胳膊上的肥肉挂在柜台上,摇着檀香扇柄,对她说:玉观音,你是观音大士还在苦海中放纵众生吗?她还能说什么?我不得不咬牙切齿地让那个淘气的女人把便宜的钱拿回来。经过二十年的长途跋涉,这没什么。只有像萧红梅等人这样的小贱人才会端着一杯酒来找她说,毕竟我们大姐是工头,而且是先中了彩票。陈老板,什么都别说了。你为什么不打我?刚才在状元楼,那个巴黎夜晚的小妓女,所有人都嫉妒得要流口水了,我也不知道陈法蓉是个什么稀罕物。难怪小淫妇以前没见过旧社会。那种姿势?在上海的时候,我拜倒在她的玉观音裙下。像陈法蓉这样有点基础的人,数不清自己的脚趾!两巴掌没毛病。她很久以前在新加坡就找人打听清楚了:一个小橡胶厂,两间老房子,前妻的孩子早已分居。她私下估算了一下,总有三四百万的身家。更不用说,试了他一个月,除了年纪大了,头顶无毛,有点挑剔,但还是个踏实的人。你怎么能怪那种从泰山国出来,一辈子在南洋受苦的人,把自己的钱看得大如天?但是阳明山庄80万的别墅,一买就通过了她金赵丽的名字。这样的老粗很难愿意为她花大钱。至于她的年龄,金大班凑近大化妆镜,使劲地推着嘴。突然,她脸上的眼角出现了几条鱼尾,上面覆盖着厚厚的脂粉。一个40岁的女人,还能判断别人的年龄吗?和陈法蓉这样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在一起,她还不知道自己对他做了多少。我不知道这个月我在向异美容院花了多少钱。拉皮肤和眉毛。——脸上没有一块肉是没犯过罪的。每次和陈老师出去,我都觉得自己像是被连枷着,戴着锁,上法庭,扎着肚子,做着假屁股,假牛奶。7月,全身被扎的金大班抓了两下肚子上滚烫的痱子,痒得不行。其次,陈老头羞于问起她高贵的几何,只好装成小丫鬟,抠着鼻子问他,你猜怎么着?三十岁?我妈的冬收!只有男人是盲目的。金大班忍不住噗嗤笑了。把他哄到三十五,吓得嘴大如茶杯,像见了鬼一样。
看他的样子,除了他那个种地的黄脸婆,他这辈子都没和别的女人亲近过。来台北看她,七魂先离三魂,我就迷上了。但是和他在一起,他多大了。金大班直起腰,一对奶子高高翘起。要收拾这样一个老人,恐怕连手指头都不用抬。
金大班打开皮包,拿出一盒美国骆驼牌香烟,点上一支,狠狠抽了两口,对着镜子点了点头。难怪她以前的姐妹都是抱个棺材板,不过也有这样的优点,省了不少麻烦。一个年轻人,怎么会这么安静?秦熊下船回来,没有让她全身酸痛?她诚实地告诉他:她是一个40岁的女孩,比他大六七岁。她怎么还有精神和他纠缠?该死的,秦熊说他喜欢大龄女,体贴又善解人意。他想要什么?你想要妈妈吗?秦熊确实对她说过:他小时候母亲就去世了,他在海上漂泊一辈子也没伤害过谁。说实话,他对她比亲生母亲还孝顺。无论他走到世界的哪个角落,他总会送她一些东西:香港的羊绒衫,日本的绣花和服睡袍,泰国的丝绸,从来不会断。还有一周一封信,十几张信纸,不知道是从什么信里来的:“赵丽我的爱”3354真恶心!他自己是个痴情的男人,却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有一次,他回来,喝了点酒,抱着她痛哭。一个彪形大汉倒在她怀里,哭得像个孩子。为了什么?最初,他在日本。他寂寞了一段时间,和一个日本女人上床了。他为她感到难过,感到难过。这到底从何说起?他把她当成什么了?还是十几岁的女学生,这是第一次恋爱吗?他兴奋地拿出存折给她看。他已经存了7万元。等五年,——。我妈——,再等他五年在船上当大副。他会回台北买房子请她做老婆。她对他苦笑了一下,却没有告诉他,在百乐门走红的时候,她一夜之间转出的钱恐怕不止这些。五年,——。五年后,她将成为他的曾祖母。十年前,金大班又吸了一口烟,伤心地想:“如果十年前,她遇到泰鸿这样痴情的男人,也许她早就结婚了。”十年前,她有许多金银财宝。当时她是故意找一个对她真心的人。上次秦雄出海,她心血来潮去基隆送他上船。码头上挤满了女船员。船走的时候,她满眼泪水,望着大海,魂不守舍。她在心里喘着气。这次她嫁给了陈法蓉和秦兄,而她连一封信也没去。秦兄不能怪她无礼。她能像那些女人一样等待灵魂吗?四十岁的女人等不及了。四十岁的女人没有时间谈恋爱。一个40岁的女人,——,甚至可以放弃一个真正的男人。那么,一个40岁的女人想要什么?金大班把一个烟头掐灭在烟碗里,想了一会儿。突然,她抬头对着镜子笑了起来。她想要一家像任黛黛那样的绸缎店,当然是她家的两倍大,而且就在她家富春楼对面。一是杀价八成,让那贫嘴刁夫尝尝,要知道我玉女神金可不只是招惹了。
“大姐3354”更衣室的门开了,一个年轻的舞者走了进来,对着金大班喊。金大班正用粉扑往她脸上扑。她没有回头。从镜子里,她看到那是朱凤。半年前,朱从苗栗来到台北。她以前是采茶工。老子是个酒鬼,后妈却被逼出来了。昨晚来巴黎,朱枫穿上高跟鞋,像踩高跷一样。不到一周,客人就被得罪了。童槐狠狠地骂了一顿,当场就要被踢出去。金大班一见到朱峰,就瑟瑟缩在一个角落里,像兔子一样,说不出话来。她实在是恨透了同德那副恶毒的样子,一气之下,就把朱凤给砍了。她拍着童的胸脯说,一个月之内,朱不会起床,她的工资将由金支付。
她真的在朱枫身上下了很多功夫。舞池十八般武艺全是她教的,她想尽一切办法为她招徕客人。朱峰也设法有所作为。半年后,她虽然没拿到顶卡,但一晚上就有十几张转盘票。
“怎么了,红舞女?你今晚翻了多少桌?”金大班见朱凤进来,在她身边坐下,一言不发,便逗着她问。刚才在状元楼的酒席上,朱枫一句话也没说,眼皮一直红着。金大班知道朱凤平日里依赖惯了,自然有点心慌。
“大姐3354”过了很久朱枫又喊了一声。金大班意识到朱峰的神色有异。她迅速转过身,看着朱凤。刹那间,她恍然大悟。
“你中毒了吗?”金大班冷冷问道。
这两三个月有个在台湾省立大学读书的香港华侨学生,每天晚上都来办朱峰的节目。那个小男生也挺浪漫的,金大班冷眼旁观。朱峰竟然很动心。她一次又一次地警告她:这只是玩票的事。当你认清真相的时候,吃亏的总是舞者。朱枫一直笑着不肯承认,却把浪漫的事情做了,没有告诉她。金大班盯着朱峰的肚子。难怪这个小骚货拿了她的肚兜露出真面目。
“人呢?”
“我回香港了。”朱峰低下头,迟疑地回答。
“你有没有落下什么东西?”金大班又追了过来,朱峰摇了几下头,什么也没说。金大班顿时觉得一腔怒火给勾起来了,这个没有耳朵的小娘们,自然是要让人吃了。不是她觉得对不起朱枫,而是她在朱枫身上的付出都白费了,她真的很生气。这样的乡下土豆很难脱胎换骨,就像一根葱,会很受欢迎。连陈大班这种世界各地的胖女人都来找她打听朱枫的身价。
她揪着朱凤的耳朵,咬着牙对她说,再坚持一会儿,你的日子就来了。玩,玩,玩,一个货腰女孩的第一大忌讳就是让人睡大觉。哪个舞者不残暴冷酷?就算你红得满天都是,一旦知道自己睡不好,就会抠着鼻子像鬼一样跑掉,好像身上有鸡屎一样。
“哦,3354,”金大班冷笑道,在台上砰的一声粉扑,道:“你大方!人家把你肚子搞大了,拍拍屁股溜了,你连他半根鸟毛都没抓到!”
"他说他一在香港找到工作就会汇款."朱峰低下头,双手擦着手帕,开始抽泣。
“你还在做你妈的春秋梦!”金大班霍然站了起来,走到朱峰身边,用力啐了一口。“你把大鱼放走了,还能把它抓回来?既然没有抓男人的能力,那就勒紧裤腰带吧。现在人们种下了祸根,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来到这里。我看重什么?平时教你的都是哪里听来的?那个小混蛋想逃跑吗?你不会拿着马桶里的沙水,当着他的面倒吧?”金大班凑近朱峰的耳朵边喝边问。
“那种东西——”朱枫反问回去,嘴唇颤抖着。“我怕疼。”“哦,——怕疼!”金大班再也忍不住了。她一手拉起朱枫的下巴,一手戳她的眉毛。“怕疼吗?怕疼,为什么不回苗栗老家做小姐?来这种地方让人搂腰摸屁股?怕疼?你有你的一份在街上卖家伙!”朱凤用手捂住脸,放声大哭。金大班也没理她。她只是点燃一支香烟,抽了起来。她在房间里溜达了两圈,突然走到朱凤面前,对她说:“明天到我这里来,我带你把那东西从你肚子里敲出来。”“啊——”朱峰抬头惊呼。
金大班看到她拼命用双手捂着微微隆起的肚子,抽搐着的脸苍白如纸。金大班不禁惊呆了。她站在朱枫面前,默默地看着她。她看到了朱凤凶狠的眼神,那眼神里充满了仇恨,仿佛一只刚被抱起来的母鸡在拼命准备偷吃它的蛋。她爱上了他,金大班暗暗叹息。如果这个小贱人真的爱上了那个小混蛋,那就没办法了。这次没尝过人生三昧的小妓女们,可能不会听你的,因为你说你舌头烂了。甚至在她自己的时间里,她为月如而怀孕,妈妈和哥哥抓住她的胳膊带她出去堕胎。她抓着自己的肚子打滚,对他们哭喊着:“要不要把肚子里的那块肉弄掉?”除非你先用绳子勒死她。母亲狠心,往脸上抹了一把药,击落了一个已经成了形状的男胎。人生中唯一一次,她真的目光短浅:吞金,上吊,服老鼠药,跳苏州河——,她都不会死。妈妈天天劝她:南,你是个聪明人。人家管家少,独子,独子,你把前途毁在哪里?你们这些卖腰的,以后拖个没爹没姓的王八蛋。谁想要你?妈妈的话不可能没有道理。
自从大官老子月如派了几个警卫把月如从他们在徐家汇的小窝里带走后,她就知道自己这一辈子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小情人了。但是,那时候她还小,也有很多愚蠢的想法:她要为自己的学生爱一个儿子,她要一辈子守着那个小恶棍,哪怕在大街上乞讨。卖腰的不是人吗?那颗心也是肉做的。
另外,是个漂亮的大学生。有几条像朱峰这样刚下海的鱼能撑得住?“拿着,”金大班卸下右手无名指上一枚一克拉半的蜡制钻戒,扔进朱峰怀里。“这值五百块钱,足够你和你肚子里的小混蛋过个一年半载了。你出生后不一定要回到这个地方。这顿饭不是你能吃的。”金大班说着,把更衣室的门摔了下来,朱凤在后面叫了几声,她都不回答。她只是跺跺高跟鞋,把它抖了出来。舞池外面早就挤满了人。雾蒙蒙的冷气里,有红绿绿的灯光闪烁,乐队打得很热闹。舞池里的一对对情侣粘在一起,像扭曲的糖果一样晃来晃去。金大班走过一个平台,抓到一个舞女。她回头一看,原来是大华纺织厂的董事长周来抱美了。
“金大班,请做一件好事。梅今天晚上脾气不好,恐怕你得努力求人,才能扭转乾坤。”周拉着金大班的胳膊,焦急地说道。
“那也要看你们周主席怎么邀请我的。”金大班笑道:
"你和陈老板的喜事怎么样,——十桌酒席?"“八卦!”金大班伸出手来,使劲摇了摇周,然后摇到了的身边,在她身边坐了下来,低声对她道,“把这张桌子翻过去。人家已经等得魂不附体了。”“随便,”萧红梅正在和桌上的几个人调情。她头也不回地走开了。“他的钱比别人多值几个便士吗?告诉他:新加坡的莫娜在等他吃宵夜!”“哦,原来是醋罐子打翻了。“金大班笑道。”呸,他也活该?”肖梅指了指她的鼻子,笑道。
金大班凑近萧红梅的耳朵,对她说:“你看我大姐姐的脸。人家要给我摆十桌酒席。”“所以你偷偷跟他勾搭上了。”萧红梅转过头,笑了。“你为什么不跟他走?”金大班没有回答,而是斜眼看着肖红梅。他一手两只手抓住了肖红梅的奶子,吓得肖红梅慌慌张张地躲起来,惹得桌上的客人都笑了起来。忙着求饶,用金大班咬着她的耳朵说:“那你得向那个周解释,他今晚完全暴露了你的光辉,但我没有饶过他。你大姐金以前去过,你听不懂‘趁热打铁’这句话。天冷了,那铁还能拉吗?”
金大班斜靠在舞池边的一根柱子上,用牙签剔牙,看着、肖红梅、姚瑶娆,走到周那边的桌子前。肖梅穿着一件石榴红色的薄纱旗袍,两条雪白圆润的手臂露在外面,肩带和手臂微微颤动。那一身的风情,别说看到火的男人,就连看到的女人都得走神。更何况她是一等一的彪悍泼妇,心狠手辣。玩了这么多年,我还没见过她翻筋斗。那个周,至少已经在她身上贴了十个二十万。我都不知道她算不算风骚。这就是成为头号舞者的材料,金大班在心里暗暗称赞。朱枫的软糖只能给她捡鞋。肖红梅虽然远没有她玉女金在上海百乐门时代的风头大,但在台北的一些舞厅里也是一品拔尖。当年,只有米高梅五虎老大吴能和她一起赴台演唱。据说两人都是九天瑶女白虎星转世,来到黄埔滩惊世。不过,她刚刚跟吴这个母虫子成了小姐妹。晚上翻桌后,两人去惠康吃炸鸡,手指头打架,哪个打得多,打得狠,打得漂亮。那些年我做了很多不道德的事。不知道伤害了多少人。为了她,玉观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后来,吴早早离开了,悄悄地嫁给了一个商人。
当时她还在纳闷,感觉冷清多了。当她来到台北时,她去中和乡看吴。没想到当年那个张牙舞爪的母虫居然化身为大佛。吴在自己家里建了一座佛寺,里面有两尊玉罗汉。她的家人说她常年吃素,连半步佛寺都不肯出门。吴没抬头看她,摇摇头,叹口气,“啧啧啧,阿里,侬还在那个地方闹事呢”听得她心里一凉。最后他们机智过人,一个个像鬼一样,嫁了人,修成正果。只剩下她一个人作为玉观音的孤魂野鬼,在邪海中游荡了二十年。该死的,她没有吴的智慧。不想去西方。难道她要学吴建佛寺,里面真的有玉观音吗?我做了一辈子的恶,让那些菩萨蒙羞!她横了心,脚一伸,就下到十八层地狱去尝尝刀脚下煎锅的滋味。
“金大班3354”金大班转身走了。她看到乐队附近有一张桌子,一群年轻人走过来,向她挥手,大喊大叫。金大班认出那是一群在外企工作的流动少年,身上有两篇文章,骨子里都是风骚。金大班也咧嘴一笑,风向标摇了摇。
“金大班,”一个叫蔡晓的打杂的捏着金大班的手笑嘻嘻地对她说,“你明天就要当老板娘了,我们的小马说还没吃你做的炖鸡呢。”说着桌上的那群男生都诡异地笑了起来。
“是吗?”金大班乐呵呵地答道,坐在蔡晓的大腿之间,使劲磨了两下,一只手勾着蔡晓的脖子,说:“我又没弄死你的小鸡,上哪给他炖呀?”说着她另一只手暗伸下去在蔡晓的大腿上捏了一把,捏得蔡晓尖叫起来。就在蔡晓双手不守规矩的时候,金大班霍然跳起来,笑着把他推开:“别跟我捣乱,你的老架子在这里。不行就教他们笑话我。”说着,几个舞女纷纷过来转桌,一个照面就让这群男生搂着舞池,贴上去跳舞。
"嘿,小白脸,你的旧相框呢?"金大班正要走开,却发现座位上有一个年轻人,没有雇舞女。
“我不太擅长跳舞。我是来看他们的。”年轻人嗫嚅着什么。
金大班不禁停住脚,上下打量着他。他只是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恐怕他还是一个在大学学习的学生。他穿着非常整洁。他穿着浅灰色西装,打着红色条纹领带。他轻松自如,浑身上下都充满了胆怯。一看就知道是第一次来舞池演野角色。金大班向他伸出手,笑着说:“我们这里不允许自由观赏。我今晚就寄给你。”金大班说着,拉着娇滴滴的小伙子走向舞池。乐队在弹《小亲亲》,一个慢了四步。舞台上,绿牡丹和粉牡丹两姐妹身着红绿,互相搂着对方的腰,妖娆妖娆的唱着:你是我的小亲亲,为什么总是对我冷淡?金大班借着舞池里的柱灯,看着那个微微仰起头的年轻人。她发现他五官很美,胡子和头发都是绿色的,长发梳理得很好,散发出一阵贝林的甜香味。他不敢靠近她的身体,只是微微搂着她的腰,僵硬地走着。走了几步后,他踢了踢她的高跟鞋。他恐惧地抬起头,羞涩地对她笑了笑,一直含糊地对她说对不起。他苍白的脸突然变红了。金大班冲他笑了笑,饶有兴趣地看着他。大概只有第一次来舞池的嫩字才会脸红,甚至来舞池取乐也会脸红。也许她只是爱上了一个脸红的男人。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去百乐门,和她跳舞的时候,我羞愧得连头都没抬,脸上一次又一次的绯红。那天晚上,她带他回家。当她发现他还是个男孩时,她把他的头紧紧地搂进怀里,贴在自己裸露的胸膛上。两行泪水突然夺眶而出。当时她心里充满了感激和怜惜,得到了这样一个腼腆男人的童贞。有那么一会儿,她觉得她所遭受的来自其他男人的所有侮辱和亵渎都随着她的眼泪消失了。她一直觉得男人的身体又脏又丑又臭。她和很多男人睡过,每次都是背过身,紧闭双眼。但是那天晚上,当她熟睡的时候,她起床了,跪在床边,在月光下看着床上那个赤裸的男人。月亮照在他白皙的胸部和纤细的腰肢上,似乎她真的第一次看到了一个裸体的男人。那一刻,她意识到一个女人疯狂地爱上了一个男人的身体。当她把滚烫的脸颊轻轻贴在月亮冰冷的脚背上时,又忍不住无声地哭了。
“这个舞我不会跳。”年轻人说。他停下来,尴尬地看着金大班。乐队刚刚换了一首曲子。
金大班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终于轻声一笑,道:“不要紧,这是三步中最容易的。你跟着我,我给你数拍子。”然后她把那个年轻人抱在怀里,脸颊贴近他的耳朵,轻轻地数着:一二三三三五四一二三三三三三五四。
这个网站是个人知识管理的网络存储空间。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不代表本站观点。请注意甄别内容中的联系方式、诱导购买等信息,谨防诈骗。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一键举报。
更多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作者(《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相关信息请关注本站,本文仅仅做为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