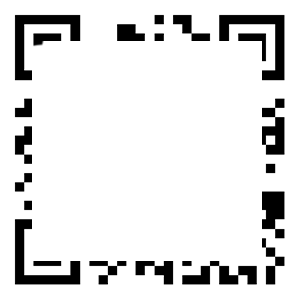广州流经的那条江叫什么江(流经广州市区的河流)
广州流经的那条江叫什么江(流经广州市区的河流),本文通过数据整理汇集了广州流经的那条江叫什么江(流经广州市区的河流)相关信息,下面一起看看。
【编者按】上周,广州首座跨江人行桥广征芳名的消息传来,满城关注,大江展新颜。但少有人记起,在开启了中国苦难深重的近代史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珠江亦承载过广州城的一
【编者按】
上周,广州首座跨江人行桥广征芳名的消息传来,满城关注,大江展新颜。
但少有人记起,在开启了中国苦难深重的近代史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珠江亦承载过广州城的一段“痛史”。
本文的作者家住洛溪岛,珠江后航道南岸。他有感于门前晨昏气象,又遍查相关史料、笔记,撰成此文,还原了180年前珠江航道失陷、广州第一次被异国的坚船利炮兵临城下的经过。今日地标林立、人们悠游信步的珠江沿岸,在那个民族衰微的时刻,忍看夷敌长驱直入,偌大的国家却毫无还手之力!
作为《羊城晚报》多年的忠实读者,本文作者托稿本报,与读者分享。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此唤起人们守护珠江、珍惜与维护今日祖国强盛的共情。
文/黄增章
每天,我都习惯在洛溪岛北部的江岸漫步,除非是朔风怒号,或大雨如注。
沿着宽阔舒适的休闲步道信步而行,看江水潮起潮落:涨潮时波光粼粼,江水汩汩而上,忽觉乾坤倒转;退潮时江水翻滚奔腾,浩浩荡荡,又有大气磅礴之叹。灵动而又变幻的江面图景,沁人肺腑的习习江风,令人心旷神怡。
每当清晨或黄昏,或是节假日,这一带总是游人纷至沓来。他们或三五结伴边走边聊天,或跑步打拳锻炼身体,或跳舞唱歌自得其乐,或忘情于垂钓,享受江畔惬意的慢节奏生活。
虽然住在这里已经有些日子了,但我对所处环境,仍有点初来乍到的感觉。
但一次歇脚攀谈时,有位老者眉飞色舞地向我介绍,几十年前江面宽多了,这一带全是荒滩,什么也没有,过江要坐轮渡。江对面以前只有管理河道的单位,现在却建起数栋几十层的高楼。远处的沥滘村不久也要拆迁,将建起更多的高楼……
这一席话引发了我尘封已久的记忆。
曾经,洛溪岛还是“满目芊芊野渡头”
我并不是没来过此地!1978年春,我就读于康乐园,我们中山大学历史系组织全班同学,去位于中山县翠亨村的孙中山故居参观。
我们早上从中大校园康乐村出发,向南行到江边坐轮渡,等船的地方对岸就是洛溪岛,当时真觉得是“满目芊芊野渡头”。而后又一路舟车劳顿,直到傍晚时分才抵达翠亨村。如今此间仿佛换了一个世界,难怪我脑海中已了无痕迹。
更巧的是,我当年本科的毕业论文选题为“道光与鸦片战争”,看到资料说,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虎门形势危急,清政府调集大军(包括四川、湖南、江西等地的兵力),部署在珠江前航道两侧,然而最终进攻广州城池的英军军舰却是绕其他水道而来,让当局措手不及。
1841年1月7日,英军舰队进攻虎门,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率守军殊死抵抗。图为关天培等指挥将士与英舰在虎门海面激战的场面
不过,当时我只是从书面知道,英军绕行的水道可能是珠江的沥滘水道与大石水道。至于这两条水道的具体位置、是何模样,则没有任何直观印象。甚至于现已在洛溪岛居住多年,其实就位于这两条水道之间,却浑然不觉。
这一番点醒,也引发了我继续研究的兴趣。我进而发现,第一次鸦片战争虽然于1840年6月爆发,到1841年2月英军攻陷虎门,3月中旬他们才沿水路上溯进犯到广州城下,距今正好是180周年!
我应该为此做点什么。于是用了几个月时间,重新查阅《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等浩繁的史料,就我所知所感,记下这些文字。
避开清军布防,英军绕道逼近广州
当年林则徐在加强虎门防御的同时,也为提升内河防御能力进行了筹划。他设想英军攻陷虎门后继续进军广州时,可能出现的情况)——
英舰进军线路只能经狮子洋(见下图①)上溯,至长洲岛(见下图②)一带就要面临选择了。因为从这里开始,珠江的主要水道自北至南分为三条:
流经猎德的北航道,又称前航道(见下图③);流经沥滘的南航道,又称后航道(见下图④);大石水道,又称三枝香水道(见下图⑤)。后航道与三枝香水道之间就是今日的洛溪岛(见下图⑥)。
千百年来,广州城池下的珠江前航道舟楫往还,交通繁忙,也是进出广州最便捷通道,自然是防御的重点。而沥滘水道与大石水道历来被视为偏僻迂回,疏于管理,清政府也没有派兵把守。
一些士绅认为,即使英军沿这后两条水道入侵,最终也必须经东塱大黄滘,才能进入白鹅潭抵达广州城下,因此将防御重点放在扼守要冲的大黄滘炮台群(见上图⑦)就可以了。
林则徐接受了这一建议,未在沥滘及大石河道派兵守卫,只是下令在较狭窄的河段填塞河道。可实施时没有预见到事态的严重,也只是草草应付,没有完全堵塞,涨潮时船只仍然可以通过。
果然,英军攻陷虎门进入狮子洋后,据《夷艘入寇记》所载:“是时定海之夷船亦至广东,共五十大艘,自黄埔至虎门,舳舻相接,遍树出卖鸦片之帜。”他们决定进攻广州城,迫使清政府割地赔款与开埠通商。
英军最初决定的主攻方向,是沿前航道挺进。但很快就碰到难题,前航道河床较浅,当时的英军随军记者在《英军在华作战记》中写道:“搁浅成为江中一切大船所这样习遇的事了,以至预料每天要发生两三次,一只船而能从一处移到另一处而不发生此事,那是幸运的了。”
他文中所说的“大船”,其实还只是装有20门大炮、排水量不足1000吨的轻巡舰。而当时停在黄埔的,不仅有装载了74门大炮、排水量达1764吨的英军主力舰,而且排水量1000吨以上的护卫舰也为数不少。这些舰船都无法沿前航线抵达广州城池之下,只能另辟蹊径。
于是英军派出舢板在各处探测水道,西至石门,西北至罾步滘,西南至佛山,以及广州番禺的市桥、沙湾等处,查探可供兵船进退的水道。
“迷宫”般的河道,20多公里走了五天
实际上,从狮子洋上溯广州方向的水道蜿蜒曲折,有众多汊道,而且潮汐落差大,例如在沥滘河段,最大落差可达1.7米。主水道中有一道常年冲刷留下的深槽,槽两岸则是宽阔的浅滩。
因此涨潮时一片汪洋,船只在水上就如同车在平原一样行驶;退潮时浅滩露出,如果不熟悉水道,船极容易开进浅滩而搁浅。沥滘水道一带又有“西海”的别名,不难想象其涨潮时一片茫茫泽国的景象了。
1841年3月5日,英军下发了兵分两路进军的命令,其中,摩底士底号带领前锋舰队经沥滘水道进军,西分队则走大石水道。或许是因为近广州城时要行经大黄滘,所以《英军在华作战记》中将沥滘水道也称作大黄滘水道。
大黄滘(又称大王滘),是指白鹅潭以南、珠江东塱段的龟岗岛,岛中与江岸上均建有炮台群(见下图)。“猎德大王滘,珠江两咽喉”,都是拱卫广州城的要塞,被英军视为眼中钉。
充当开路先锋的轻巡舰摩底士底号装有20门炮,行驶灵活,逆风性能好。1841年3月8日,摩底士底号驶入沥滘水道。“溯流而上,居民群涌到两岸来观看这样不平常的一幅景象。摩底士底号一定是见于这条支流的第一只‘大船’。或许由于这里没有防御工事,中国人不知道水量是足可以供船只行驶的。”
后面陆续跟进的有包括武装汽船、轻巡舰等数艘“大船”,另有三个小船队,都是其他护卫舰所属的武装小船,临时抽调过来。
英军从8日进入沥滘水道,到13日开始进攻大黄滘炮台群,仅仅20多公里的路程他们花了将近五天!其实,因清政府没有派兵防御,英军在此期间所受到的唯一阻碍,只是“杂乱的水道和大江的支流所形成的”、“迷宫”般的河道。
随军记者曾记下摩底士底号爱尔斯船长的遭遇——“(他的驳船)在返回大船的途中,在杂乱的水道和大江支流所形成的迷宫之间迷路,最后因为潮水退落,把船搁在稻田上了,他和他的小船船员就在这里过夜。”另一艘作战能力较强的前锋号,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开过浅滩,接近大黄滘了”。
从这些记录中,可略知当年沥滘水道的状况之复杂。因此,前锋舰队在前进过程中最主要是要测量水道,避开浅滩,找出深槽,规划航道,引导后续部队前进。后来,装载了74门大炮的主力舰也溯流而来。
激起民愤,英军怕后路被断匆忙撤退
得知英军由另外的水道挺进,清政府急忙调集大军加强大黄滘、凤凰岗、芳村花地一带的防御。3月17日、18日,双方在凤凰岗与花地一带曾有过一番激战,但已无法阻止英军兵临广州城下。20日英军进入白鹅潭、西关,前航道两岸的炮台被英军自西向东悉数摧毁。
此后两个多月,入侵者屯兵沙面、白鹅潭、大黄滘一带,时刻威胁着广州的安全。钦差大臣奕山草率用兵,招致英军报复。1841年5月24日,英军自东南西三面攻打广州城池,随后占领越秀山上的四方炮台,26日炮击贡院奕山住所。
这位慌了神的钦差大臣下令在城墙上竖起白旗,于27日接受义律的五项条件,签订《广州和约》。英军要求清政府一周之内交600万元“赎城费”,付清款项后,他们才退出虎门之外。
清政府怯懦妥协,而民众却在奋起反抗。侵略者的强盗行径引起广州人民的愤怒,5月30日、31日两次包围四方炮台,“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因义生愤愤生勇,乡民合力强徒摧。”“老弱馈食,丁壮赴战,一时义愤同赴,不呼而集者数万人。”
据同治《番禺县志》所载,“是时南海番禺两县团勇演练,义律知粤市不可复开,遂往攻厦门。”
见此情形,因为担心民众将水道堵塞,被断了后路,6月1日英军在只收了部分赔偿款的情况下就匆忙撤退了。
沥滘水道竟还有个别称,叫“义律航道”
是次英军退出虎门之后,广东当局就开始组织堵塞珠江广州段的三条河道。后经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再次填堵,从此这些水道基本只能供渔船与帆船通行,由虎门而来的“大船”再也不能从水路直接进入广州,海运而来的大宗货物要在黄埔港转装于木船才能进广州,阻碍了广州航运货运业的发展。
抗日战争胜利后,宋子文主政广东,试图改变广州的航运状况。但因为前航道还是太浅,而大石水道的疏通工程量又过大,于是他授权珠江水利局1948年9月开始疏通沥滘水道,到1949年1月沥滘段初步通航。
笔者多年在文博单位管理1949年10月前出版的报刊,不止一次发现在有关疏通沥滘水道的报道中,有用“义律水道”来代称的现象,令人奇怪。
另有1949年出版的《广州进口水道沥滘段通航纪念》一书,书中的英文部分均用“义律水道”来称呼这条水道。由此可知,沥滘水道确实除了后航道、南航道、大黄滘水道等别称之外,还有一个名字叫“义律水道”(Elliot Passage)。
原来,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策动者、英国驻华全权公使查理·义律(Charles Elliot),1841年3月也乘坐武装汽轮“复仇神号”,加入了取道沥滘水道的前锋舰队。他打算与清朝的钦差大臣奕山直接打交道,“复仇神号”的桅杆上还挂着一面白旗,表明上面乘坐的是来谈判的全权大臣。
由于义律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作为”被英国政府认可,他们就以入侵者的姿态,把这条珠江水道用“义律”来命名了。
这也是傲慢的英国人在以“发现新大陆”的殖民主义惯性思维,来看待这块土地。广州城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而且未有河南,先有沥滘村”,自明朝开海禁之后,这里就是广州南面最重要的商品集散地。“沥滘水道”之名已有几百年历史了,哪里用得着入侵者万里迢迢地再来命名!
泽国成热土,珠江大动脉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时光荏苒,社会变迁,如今前航道与大石水道已不再作为货物运输的通道。沥滘水道则经过多年的疏通和一系列整治,已经成为珠江水路运输的大动脉。
据业内人士说,因受最高水位时桥梁净空高度的限制,这里只允许通行排水量5000吨以内的船舶。即便如此,通过江海联运,它仍成为广州乃至中国南方货物运输的重要通道。每天,集装箱货轮、 散装货轮以及油汽轮船等各式各样的船舶,昼夜不息,穿梭于这条大动脉之中。
如今跨越这条水道,再也不用“隔岸渡船呼不应,柳荫深处立多时”。从康乐园去翠亨村,大约只需要一个半钟头。多座快捷的大桥连接着高速公路,以及地铁、公交,将来还有隧道,共同构成日趋完善的公交系统,令两岸经济焕发出勃勃生机。
千百年来的茫茫泽国,已变身为富庶的一江两岸,后航道经济带的建设正稳步推进,它将是集文化创意、都市旅游、人工智能、海洋科技等产业于一体的服务型经济带。
我沿着步道前行,隔岸遥看对岸的沥滘村。180年前,这古老村庄里高大精美的祠堂建筑,曾因为被英军误认作炮台而遭炮击。而后,在愤怒的呐喊声中、在巨大的苦痛中,乡民们用排椿大石筑起两道拦江堤坝,试图阻止“船坚炮利”的侵略者施展其“奇技淫巧”。
时至今日,航道中央及两旁的防御堤坝早已清除,门户大开、深掘河道,任由船舶通行。然而,哪个强盗还敢再将军舰开进来耀武扬威、肆意妄为呢?还有哪方妖孽,敢在这里“树帜出卖鸦片”!
每当一轮满月悬挂在江面,明月向四野撒下柔和的清辉,水面氤氲出薄薄的雾气,水天相接,朦胧缥缈。两岸黛色的树影,远处巍然而立的楼宇,大桥的雄姿,以及点缀其间星星点点般的灯光,还有闪烁着红绿光芒的航标灯、缓缓而来的船舶信号灯,组成一幅如梦似幻的画面,让人感受到温馨、安宁与满足。
180年的岁月流逝,足以磨灭很多记忆。然而,我们不应忘记这里曾鬼魅般驶过的异国战舰、遭受的异国炮火,更不能忘记列强欺凌给我们民族带来的苦难、屈辱与悲怆!中国在崛起,如今的光景实在来之不易,值得每一个人珍惜与守护。
本版黑白老照片出自《广东百年图录》(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纂)。鸣谢该馆倪俊明副馆长对本版的大力支持。
更多广州流经的那条江叫什么江(流经广州市区的河流)相关信息请关注本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