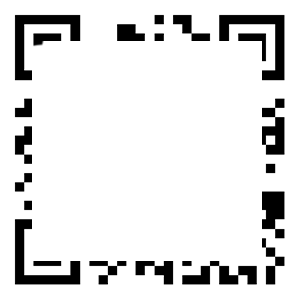桐城派 新文化(桐城派的形成)
桐城派 新文化(桐城派的形成)、本站经过数据分析整理出桐城派 新文化(桐城派的形成)相关信息,仅供参考!
桐城派文化的发源地(新文化运动与桐城派)桐城派作为传统文化社团参与了此次盛会。作者:任学山(合肥大学副教授)
在现代学术史上,桐城派通常被视为一个文学流派。当然,这是好的。桐城派以文章著称,素有“天下文章,皆在桐城”之称。但另一方面,也不尽然。桐城派产生于清初,延续到清朝第一代,余波一直延续到民国。显然,这300年的基业,不是单靠文章就能支撑的。如果我们深入了解桐城派,不难发现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流派。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艺术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纵观桐城派300年的发展历程,不仅诞生了方苞、方冠诚、陈永光、邓廷珍、姚颖、曾国藩、郭嵩焘等一批朝廷大员,而且在禁烟、饮酒、治河、边防、护疆、治军、贸易、洋务等方面都有建树。郭嵩焘、黎庶昌、薛福成等派往欧洲的一级外交官,是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先驱。孕育了姚鼐、吴德玄、曾国藩、祁俊藻、张裕钊等人的书法、碑刻艺术,与桐城派文章相辅相成。同时,几乎所有的桐城派人物都有着丰富的教育经历,从在翰林院任教,到在省一级学习政治,再到书院负责人。可以说人才辈出,影响深远。由此看来,桐城派其实是一个真正的文化学派。在众多流派的成员中,虽然跨越了地域时空的限制,但他们都遵循着大致相似的学术理念、价值追求和精神诉求,彼此相通,代代相传,形成了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共同体。
作为典型的传统文化群落,桐城派的诞生和兴衰具有范式意义,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总之,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察。
首先,认同观念是传统文化共同体形成的思想基础。社群是一群人* * *,它的相互凝聚力是建立在价值认同和意识形态归属上的。伊佐尼认为,共同体的形成无非是两点,一是紧密交织的关系,二是共同的价值规范和意义。从桐城派的生成史来看,古代文学修辞经世济民已有三百年,而连接修辞经世的思想就是义与法。义是经学和史学中第一个流行的概念。后来,方苞把它引入修辞学,创造了古义法。简单的讲法,意即有物,法即有序,两者合为一篇书面文字。他说的不是想象,而是来自现实,寄托着济世济民的伟大志向。前言不是一堆文字,而是字里行间流淌的生命气息。义与法既是气质与尊严的统一,也是德行与辞令的统一,是立言与立功的统一。后来刘大奎发展了义法理论,强调文人的能力,通过字和音节实现文章的空气,在吟诵和叹息之间清理精神的大厦,在呼吸和俯仰中贯通古今。在《药乃》方、刘的基础上,吸收了《干甲》中的考据方法,将其与义、考据、考据融为一体,使义、考据可穷尽,考据可穷,考据、考据可表其意,最终实现了义、考据、考据的统一。这种既想真善美合一,又想儒道文三家合一的三位一体理论,体现了姚鼐“道艺合一”、“天人合一”的理论。曾国藩介绍姚家世,除了理、考、辞之外,增加了对经济的研究。经济在孔子那里是政治事务的一个分支。四者中,曾国藩重义理,坚持桐城派的一贯立场,但他强调富国强民是其思想的根本。于是,曾国藩博采众长,学了百经百史,学了思辨的思想,帮助了百姓,繁荣了桐城,开辟了一片新天地。晚清时期,严复、林纾在桐城译介西学,启迪民智。他们和无数仁人志士一起,推动了中国社会从古代到近代的变革。可以说,桐城派已有300年历史,延续几代,弟子超过1000人。总的来说,他们都遵循相似的价值观,把辞藻和学问与基础结合起来,把个人命运与时代、家国联系起来,与时俱进,爱民如命。
第二,师生关系是构建传统文化共同体的基本路径。社区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群体有意识的组合。不同类型的社区以不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托恩尼斯社群分为三类:血缘社群、地缘社群、精神社群。这三种社区也对应了三种社区的建设方法。一是以血缘为中心的家族共同体,二是以地缘为中心的地域共同体,三是以价值观和信仰为中心的精神共同体。精神共同体是一种综合的共同体形式,它结合了前两种共同体的特点,“形成真正的人性的、更高的共同体类型”,文化共同体是精神共同体的主要存在形式。作为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群落,桐城派的基本建构方式是向师学习。桐城派的师生关系涉及人数众多,持续时间长,呈现出复杂的具体形式,大致可分为私教、公教、家学三类。私教包括三种:在家设库,拜访老师,在门外告诉别人。如在宝应时曾受刘聘用,教授、刘、刘师叔,刘氏兄弟成为他的正式弟子。范当下与的负面经验、薛福成与曾国藩的文学经验等。都成了一段佳话。门外传指的是随意的指令或书信,如的唐,梅曾良的杨。起初,方苞和陆大奎只是偶尔碰一下对方。他们晚年退居金陵后,渐渐有了联系。相对而言,刘大奎与姚鼐的交往更多,古诗词古文的讨论也比较频繁。公教主要指翰林院和书院两种教学。方苞曾两次在翰林院教过庶吉士,洪磊、褚锦官、陈大寿都是在这一时期加入方门的。姚鼐的弟子主要来自姚鼐的书院,方、梅增良、管彤、刘凯是姚鼐书院的名师。如秀峰书院的朱祁、彭毓瑶、吕晃,莲池书院的姚永冠、尚、傅增湘、高步亭、等。相比较而言,家庭教育是围绕血缘关系产生的师徒关系,既包括家庭中的子侄,也包括亲戚公婆。
桐城派除了上面提到的师徒关系,还有两个重要的学术关系,一个是师生关系,比如教务,乡会中的考官,一个是仰慕他的学业却没有机会亲他的私人弟子。前者属于科举时代的有教养的老师,与有教养的老师相对,对个人和群体的发展都很重要。私塾弟子虽然不以师徒命名,但摆脱了具体授课的地域限制,迅速扩大了社团的边界和范围。如姚鼐中的曾国藩、吴德玄、王先谦等人,尤其是曾国藩对桐城派的繁荣和延伸,将桐城派推向全国,曾门弟子继续大业,传播扩散,蓄势待发。从此,桐城派再无大师。随着新文化运动,他们已经不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综上所述,桐城派文化共同体的形成是以学师关系为基础,血缘和地缘关系为两翼,私学教育为支撑。师徒、姻亲、乡党、私塾共同构建桐城派的共同体。
第三,互利共生是传统文化社区发展的基本保障。作为一种集体存在,文化共同体不是一个想象中的群体,而是一个功能性的共同体有机体。社群之所以能聚集大量的人,有些人甚至长达上百年,不仅仅是因为其成员有着共同的理想信念,更是因为他们是一个互利共生的群体。社区的核心吸引力在于能够帮助成员解决实际问题,促进其可持续成长。桐城派作为清代最典型的文化群落,解决了当时士人普遍关心的问题。众所周知,在科举时代,读书做官是无数读书人的梦想,所以如果能有效帮助读书做官,就会得到读书人的支持。桐城派的主要成员都是文章大师和老师,这使得他们掌握了文章的秘密,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 * *。无论是方苞的义法,还是刘大奎的以声求怒,还是姚鼐的义理考据,都为如何写好文章提供了清晰可行的路径。不仅如此,桐城派还将文章的思想融入教科书,方便了更广泛的学者学习,为社会不断补充新鲜血液提供了支持。如方苞主编的《钦定四书文》,是明清时期唯一的官方科举教科书,不仅为科举当局提供了权衡的准绳,也为士人揭示了写作的瞬间。这本书出版后,很快被京城和诸侯颁布,成为学者研究的范本。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也因编纂精良而受到学者追捧。可以说,桐城派的文章讲求礼义,易学易用,利于科举,这才是桐城派得以延续三百年的真正秘诀。当然,除了正常的功能,桐城派还有一些额外的加持。比如借助著名专家的推荐,可以获得发展机会。比如刘大奎,进京科考时被方苞推荐,一举成名。其次,通过教师的名气,可以获得更好的专业岗位。方苞任馆副馆长时,曾先后引进陈大寿、关显耀、赵等弟子入馆修书。第三,从事共同的事业。邓廷桢任安徽巡抚时,曾引梅增良、管同、方、吕继缇、宋翔凤等桐城派成员加入其幕府,担任政务参赞。曾国藩在吴汝纶办洋务、改良教育的同时,也有大批桐城派成员参与其中。
不难发现,群体给予个体的成长越大,对个体的吸引力就越大。另一方面,通过个人的不断参与,集团得到了持续的发展和繁荣。桐城派社团的三百年历史是无数个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尤其是一些做出突出贡献的标志性人物。创立之初,以方耀为旗手,尤其是姚鼐,承前圣贤,构建文学谱系,培养弟子和大师,编《古文辞类纂》,为桐城派开疆拓土。后来曾国藩升中原,顺从姚鼐,引湘乡、光大桐城,把桐城派推向全国。民国末年,马启昌、姚永普兄弟虽烧了药膏,也无力回天。桐城派作为一个群体隐退到历史深处,更多的学者奔向新社会。于是,在文化共同体内部,群体因个体的强大而繁荣,个体因群体的加持而发展。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当然,不难发现,桐城派作为一个传统文化群落,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不仅是因为其庞大的规模,也与现代学术研究的性质有关。对于大多数非桐城派学者来说,他们对桐城派的认识主要来源于文章,因此他们视桐梓为
更多关于桐城派 新文化(桐城派的形成)的请关注本站。